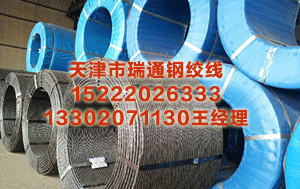黑河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美国故事正在走向终结吗?

电影《粗野派》
上周六(1 月 3 日)凌晨,特朗普政府发动袭击,逮捕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并将其押送至纽约接受审判。
这一举动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争议,也再次将美国置于一个熟悉却尴尬的位置:一方面,它以“自由”“法治”“正义”等普世价值的名义行事;另一方面,它实际采取的政治手段和军事行动,却与它所提倡和参与建立的国际秩序不断错位。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而是嵌在美国对自身角的理解之中:它既将自己视为价值的守护者,又不断在现实政治中行使强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单读为大带来10 本入美国现实的书籍,一起回望那个一度具吸引力的“美国故事”。它曾经定义着个人的自由与幸福,讲述着白手起的传奇;它也曾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参照,是文化多元化与经济市场化的标杆。可如今,当我们再次谈起美国,它却更多出现在互联网上的调侃段子里。
笑声背后,如何理解这个仍处于全球叙事中心的国?那个曾经举世瞩目的美国故事,是否正在走向终结?
01
当“自由”变成对外干预的理由
冷战结束后,美国曾满怀自信地认为:只要以自由主义为旗帜,就能重塑世界。民主会在全球扩散,开放市场会带来繁荣,国际制度会依照美国的形象建立,全人类将共同迈入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
于是,美国试图把尽可能多的国改造成民主国,动经济度相互依赖,建立国际制度来锁定秩序。但国际体系的现实却与之相悖,各国的历史、文化、族群与制度迥异,没有谁能垄断对“美好生活”的定义。自由主义思想把个人当作原子化的行为体,相信无数人的私利汇聚起来就能产生共同利益,却几乎无法提供任何维系社会的情感纽带。
美国越是行自由主义扩张,越频繁地陷入战争泥潭。从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直接军事干预,到在乌克兰冲突中的结构介入,接连不断的冲突一次次提醒我们自由主义扩张的现实限度。美国不仅没有让世界更安全,反而因为对外战争而成为一个度军事化的国。
米尔斯海默的结论直指美国梦的外部投射:如果说美国曾让世界相信自由与平等的可能,那么这种强行输出理想的方式早已走到尽头。他呼吁美国回归现实主义与克制,把力量用于在国内建设真正有吸引力的民主体制,而不是一再发动“正义的战争”。只有这样,美国才能重新赢得他国的尊重,也才能保住自身赖以自豪的自由。
02
美国梦如何埋下了分裂的伏笔
个人主义也许是美国鲜明的文化符号:自力更生、白手起、自由立。它构成了美国人想象自身的核心叙事,也是“美国梦”赖以展开的价值前提。
作者带我们溯回杰克逊时代的美国,在那样一个国力量快速扩张的年代,“自力更生的拼搏者”“自然权利的拥有者”“白手起的英雄”这三种神话逐渐成形,并被不断重复,塑造出一个充满自由与机遇的理想国度。它们既回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也成为“美国例外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是一个社会还未完全被资本垄断、社交隔阂或出生地固定化等现象所俘虏的年代。这些神话给民众勇气,也给社会提供希望。他们看到自己不仅可以“动起来”,可以参与国项目,还可以从农业飞跃到工业,从偏远小镇移居城市,从边缘进入公共话语。
试想一个没有庭背景的年轻人,只有一座农场或者一间小店,但只要靠自己的双手,就能耕种、收获、变出一条人生的新路。试想一个人只要参与政治活动、投票或在公开演说中承担起公民身份,就能分享美国的自由和权利。这就是曾经动人的美国故事,它不仅描绘了理想的自由与可能,也提供了身份认同与希望。
但今天,当我们回望这些神话,却有更多的追问:那些曾被赋予普遍的自由与机会是否真的普遍?谁能被纳入“自由人”的范畴,谁被排除在权利之外?个人主义既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也是一种遮蔽的幻象。它支撑了美国梦的活力,却也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伏笔。
03
成功学,如何变成一种惩罚
优绩主义也曾是美国故事的信条:相信机会平等,凭实力往上爬,靠努力改变命运。而耶鲁大学教授马科维茨却在《精英陷阱》中提出:恰恰是优绩主义本身,正在制造新的不平等。
对于精英阶层而言,优绩主义早已成为一种沉重的枷锁。父母为孩子精心筹划教育路线,每一次考试、每一次展示都被视作关乎未来的关键节点。成年后,他们进入名利场,却发现竞争并未结束——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让“不进则退”的焦虑几乎贯穿一生。看似光鲜的成功,往往意味着的自我剥削。
与此同时,那些被排除在精英轨道之外的人,也不得不接受另一重羞辱。优绩主义营造了一种崇勤奋、蔑视懒散的氛围,把结构的排挤伪装成个人能力不足或努力不够的结果。于是,这场竞赛的失败者既失去了机会,又被迫背负各式各样的道德指控。
正如马科维茨在书中所说:“美国的优绩主义已经发展成了它初旨在对抗的东西:一套将财富、特权和社会地位集中起来并实现代际传递的机制。”如何处理这一困境,或许正是美国故事须直面的难题。
04
黄金年代之后,普通人去了哪里
“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任何中毕业生几乎都能在本地工厂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如果再有大学文凭,机会更是近乎无限。”但《下沉年代》讲述的,正是这场繁荣退潮后的失落与挣扎。
迪恩·普莱斯出身南方烟草世,曾以为只要努力就能打破世代贫困的循环。他开过加油站,办过快餐店,又满怀热情投身生物柴油产业,想为乡重建经济闭环。可终,他在经济危机和大企业的夹击下破产,只能开着破车游走各地,向政客兜售自己的能源计划。
杰夫·康诺顿则来自精英阶层。他在大学时被拜登的演讲打动,决心一生追随这位政治偶像,先是为竞选奔走,后来成为参议院的智囊,力图动对华尔街的监管。可当拜登终于成为总统,他却因过往的说客身份被排除在白宫之外,眼睁睁看着理想与忠诚被政治机器吞噬,终失望离开华盛顿。
这是生于战后黄金年代的一代美国人:他们曾满怀希望,却在中年时亲历传统社会结构的坍塌。帕克并不只写个人的悲欢,而是把镜头不断拉远,捕捉更大的社会画卷:操纵民意的政客、不断扩张的资本、浮浮沉沉的文化偶像,乃至数以万计在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中迷失的普通人。他们的经历,是曾被美国梦的繁荣光景遮蔽的另一面。
05
在富裕的国,无可归
黄金年代的幻象崩塌之后,还存在更严重的生存困境:住房。住房本该是基本的生存保障,被“扫地出门”不仅意味着失去住所,更意味着庭关系的破裂、生活秩序的坍塌、孩子学业的中断。
社会学德斯蒙德花费多年,入密尔沃基的底层社区,与被驱逐的房客、收取额租金的房东面对面,预应力钢绞线用调查和访谈记录下赤裸的生存现实。他发现,一次驱逐往往将一个庭向社会底层。与此同时,那些破败、潮湿、时常停水断电的房屋,却能在市场和制度的缝隙中持续制造暴利。
德斯蒙德记录下被驱逐者的日常策略:有人小心保留自己与亲友的关系网,不敢轻易求助,以免耗尽后的安全绳索;有人用一个月的食品券换来一顿的大餐,好像要在困境中为自己保留一点尊严。理计算在这里往往失,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在一次次打击下继续生存。
这本书迫使我们追问:在这样富裕的国里,为什么有一方屋檐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房东、房客、国政策与私人住房市场交织的关系网络中,谁在获利?又是谁在为贫穷付出代价?
06
那些被美国梦抛下的白人
当我们谈论美国的问题时,常常忽视了一个群体:底层白人。他们被称作“white trash”,一个带着污名的词,却是美国历史中始终存在的影子。
政治文化学者艾森伯格走进美国四百年的历史,追踪这个群体的形象如何被塑造、固化乃至利用。殖民时期,他们作为英国社会的“弃民”被倾倒至北美,成为边陲农民与廉价劳动力;在工业化的洪流中,他们长期徘徊在自耕农与流浪汉的身份之间,与黑人奴隶的境遇相去无几,却因肤而被认为无需解放。即便在“人人平等”的立宣言中,他们依旧是缺席者。到了 20 世纪“优生学”盛行的年代,多个州甚至通过法律对他们强制育,以此“净化”社会。
2016 年,特朗普的胜利让这一群体浮出水面;2025 年他们再次成为保守主义的主力支持者。政客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甚至把自己装扮成“从底层走出来的一员”。这是美国的另一段历史:除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理想叙事之外,还有这样一个被遗忘了的阶层,如今成了政治格局的关键变量。
07
跨不过去的,不只是立场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支持特朗普?为什么他们一方面坚信“政府不可信任”,另一方面却对保守主义的叙事充满热情?
社会学霍赫希尔德在路易斯安那州扎根五年,入茶党(2009 年初兴起的美国财政保守主义政治运动)大本营,倾听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同理心之墙”: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并非缺乏事实沟通,而是缺乏对彼此情感的理解。当地人感到自己被精英阶层和媒体长期忽视,尊严无人看见;他们的焦虑不仅来自经济停滞与社会衰落,更植于庭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于是,他们构建出一套自洽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将支持保守主义作为捍卫自我价值的姿态。
这本书颠覆了外界对“红脖子”的漫画式描绘,展现出一群真实而复杂的人:他们的生活既有辛劳,也有自豪;他们的愤怒常常带着合理,却又被政治叙事不断操纵。霍赫希尔德怀着同情和耐心,把这些声音带到公共视野之中,让我们看到美国化政治背后的情感逻辑,也提醒我们:要理解当代美国,不仅要关注选票和政策,更要越过那堵“同理心之墙”,认真倾听这些陌生而又熟悉的故事。
08
政治如何变成一场末日叙事
“敌人在暗处密谋,末日即将来临,我们须坚守真理阵营。”半个多世纪前,历史学霍夫施塔特为这种思维模式取了一个名字:偏执狂风格。
在他看来,这种风格的核心是受迫害感:敌人不仅要击败我们,更要摧毁我们的文明。政治由此被塑造成一场非黑即白的善恶对决,毫无妥协余地。从麦卡锡主义的反共狂热,到今日社交媒体中层出不穷的阴谋论,偏执狂风格一次次在美国历史中卷土重来。它让人们同时受困于现实与幻想,使政治话语充满戏剧、敌意与不稳定。
霍夫施塔特以美国右翼为例,揭示这种思维模式如何以末世论语言强化阴谋论的力量。他提醒我们,政治不仅受利益驱动,更受人们感知与理解方式的影响,“想象的敌人”往往会引发真实的冲突。
正因如此,偏执狂风格并不限于美国右翼,它可以出现在不同国、不同派系的政治叙事之中,令公共生活受制于敌意与分裂。理解这一点,也许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的叙事为何总伴随着对危机、阴谋与末日的想象。
09
在这个世界上,小人是不讲道理的。你若谦让一步,他就得寸进尺;你若沉默不语,他就骑在你头上作妖。
一场本可以成功的平等实验
回看十九世纪美国内战结束时,战争虽然带来巨大的创伤,也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如何在奴隶制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如何让四百万被解放的奴隶真正成为公民?如何让普遍自由与跨种族平等落地生根?在那个历史转折点,美国人曾经满怀理想,相信他们可以迎来一场“二次建国”。
历史学方纳将这段被称 为“重建”的岁月写得 恢弘 而复杂: 新的宪政原则诞生了,黑人获得了选举权,南方社会出现了黑人自由劳动与参与政治的新景象。方纳特别强调,“重建”并非单纯的政策调整,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验——在国会的辩论厅里,在南方种植园的土地上,人们都在探索如何创造一个平等的国。理想与斗争并存,创造与暴力交织,那些曾经没有发声权利的人一次成为共和国主体的一部分。
然而,现实的阻力也同时显现。“白人至上”的复辟来势汹汹,制度的排斥和暴力恐吓让少数族裔新获得的权利被侵蚀。当种族平等与公民权益再次成为今天美国的核心议题,方纳的书提醒我们:那段未竟的革命,仍是当代美国故事里的裂口。
10
美国梦会结束,但理想不会
谈到美国,人们往往先想到的是它的科技实力、军事霸权或资本市场。但事实上,有一种更隐秘、却也更为持久的贡献,来自于美国的人文学科。如果说经济与政治的困境不断揭示着美国故事的裂缝,那么人文学科则承载着它为理想化的面貌。
二战之后,美国学界有意地塑造了“人文学科”这一范畴,把它作为国理想的文化表达。正如本书作者杰弗雷·盖尔特·哈派姆所说,人文学科并不仅仅是学院里的学问,它与幸福感和充实感密切相关,能够化人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探索生活的广度与度。人文学科源自对生命本质问题的批判思考,由此给予人内在的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培育出同情与理解他人的能力——而这正是民主政治与公民精神不可或缺的基石。
当然,当今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国,似乎都在经历着一场下沉。大学课程被削减,功利主义占据我们的语言,人文学科变得“过时”。不过,当文化与思想越了政治,人文学科所代表的思考能力仍能被调用,人文学科的理论积累依然能全球范围内为自由与尊严提供想象力和语言,也依然在为那些在困境中坚持对话、坚持想象更好世界的人提供力量。
美国故事的“终结”或许意味着某种幻象的消散,但它同时也让我们重新理解:没有哪一个国能垄断理想,理想需要在每一代人、每一个社会中不断重写。
撰文:Iris
手机号码:15222026333编辑:菜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