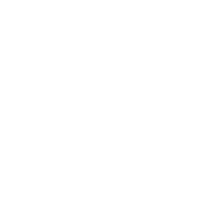齐齐哈尔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高世名:新中国音乐的人民史诗——写在《人民音乐》创刊七十五周年之际
发布日期:2026-01-12 13:48 点击次数:98

今天天气很冷,我们的心里很热。因为我们在这个会场中感受到了诸位对中国音协和《人民音乐》的一片热忱,更感受到了大家对音乐的真诚与热爱。
刚才四任主编的感言,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四个主旨发言,求真务实,纲举目张。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大家都带着一种诚意——正心诚意、真心实意,这就是中国音乐界的优良学风,为此我代表中国文联向大家致敬。
《人民音乐》没有选择学术C刊的路数,就是希望保持一种艺术本身的敏感性和自由度,一种与音乐界的人和事、问题与现象之间的紧密关联。这里我想说的是,一本杂志既要登高望远,又要脚踏实地,它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统一的。因为现实是一种实现,是已经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洛赫说:“没有可能性的现实是不完整的,没有未来愿景的世界是不值得看的。”《人民音乐》不只是要反映音乐界的现实,它所参与的是一段正在生发着的历史,它所探索的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世界。所以,《人民音乐》与音乐界的关系,如同音乐与世界的关系,既内在又外在,既反映又回应,不只是反映事实的镜子,更是照亮现实的灯火。
正因如此,《人民音乐》不只是一本专业期刊,它是一份新中国音乐史和精神史的珍贵档案。过去几天我浏览了《人民音乐》数十年的目录,感觉像在看一场进行中的文献剧,这部剧延续了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音乐史上所有的主题与形式、创作与研究、论辩与斗争……,都在这个剧场轮番上演。那些杂志封面人物是剧中的重要角色,那些大专题、大讨论则是剧中的一幕幕重要情节,中国音乐界的历次潮流和运动都是“歌队”之赞颂。今天我们纪念《人民音乐》创刊75周年,也是在梳理和回顾中国音乐界75年的历程。因为这本期刊所呈现出的,是中国音乐与社会共同谱写出的一部史诗——新中国音乐的人民史诗。
手机号码:13302071130《人民音乐》是中国音协的机关刊物,以“人民”为名,它的根基是人民史观。它的创办者们相信,在最平凡的人民生活中有很积极的东西,那是一种持久而强大的力量,根植于无数普通人的生活世界、芸芸众生“情-感-意-识”。人民,这无数“日常生活的英雄”,他们的生命实践、情感和故事,正是所有艺术感觉、知识、方法、灵感的根源,也正是音乐艺术主体性、创造性的土壤与基石。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论述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在这种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讨论“人民”和“人民性”。2012年10月,我在上海组织了一场研讨会,主题是“人民的名字”,旨在探讨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中,“人民”具有的丰富意蕴。人民的名字,中文语境中有生民、草民、公民、群众、大众、公众、诸众、乌合之众,还有黎民百姓以及芸芸众生……,英语中则有people/citizen/crowd/public/mutitude/commune……,无论中西,这都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家族。中国新文艺的百年历程,正是中国文艺通过创作实践与社会运动逐渐发现人民、逐渐建构起艺术人民性的过程。对中国来说,人民不是乌合之众,不是mutitude,而是组织起来的、觉醒的历史力量;就艺术而论,人民不但是创作的主题,更是创造的主体。
在当代中文语境里,“人民”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主体,既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社会共同体,又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熏染下的文化共同体,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他进一步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人民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不是空洞的宣传口号,而是具体、生动、复杂、多元的社会存在,是无数普通人的精神性的集合。
各位同仁,音乐不只是“独立个体的自由创作”,更关涉到国家、民族、时代、人民,关乎自然世界以及形形色色的他者。音乐家不是与世疏离、特立独行的孤绝个体,而是在“人-民-群-众-我”的复杂关系中构建出艺术家自我的主体位置,继而追求“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人民音乐,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它承载着人民的经验与心事、记忆与梦想,焕发出人性的隐微、人道的尊严、人格的光辉。
最近这一年,我一直在补音乐的课。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根植于有情世界,其至高追求不是抽象,不是形而上,也不是太上之忘情——纵然山高水长、天地悠悠,乃至地老天荒,中国音乐仍然要回向于这有情世界、芸芸众生。所以中国音乐美学中,不只有黄钟大吕、高山流水,还蕴籍着许多曲折萦回、一言难尽的人间情味。
中国文学艺术的社会意识和精神追求,从源头上讲可以追溯到“风、雅、颂”。尽管这些年《人民音乐》发表内容上似乎以“雅颂”为主,但是以我个人的理解,从观念上它的起点是“风”。古人论“六艺”:“《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这几年我思考较多的也是“风”。
《诗大序》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诗”所关切者不止于个人悲欢,更在家国天下,故而能“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这里的“一人”,不是现代主义所谓遗世独立的孤绝个体,而是具有社会意识、民生关切之“仁心”的人——其“仁心”之挺立愈高远,其所“览”所“言”者愈广大。
“风”承载着国人对自然的感兴、对世道的感悟、对人道的理解、对命运的期许。通过“风”,我们得以真正地看到“民”,看到百姓经验中默默印证着的情感与道德、生命意义和价值伦理。这种“风”的艺术、这种艺术之“风”,从人间最底层兴发,饱含世道人心,化育为普通人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常在常新,生生不息。
然而,自魏晋六朝以降,风雅颂失序了。我说的不只是文学史上所谓的“变风变雅”,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文化史与艺术史上,“雅”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的审美主流,从民众生活现实中来的“风”逐渐退隐,甚至连“风雅”都联缀为一个审美概念。当风雅成为一个概念,“风”就消亡了,只剩下“雅”。在美术领域的表现是,自五代开始,山水、花鸟成为主流,人物画渐趋边缘,人逐渐退场;自元代起,文人画成为主流,宫廷画师、民间画工和匠人制作都被打落尘埃。
直到二十世纪,随着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展开,一种新的人道彰显开来。一方面,林觉民式的“家国情怀”、国民革命的“主义理念”,塑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革命情怀(与儒家传统的“革命”观全然不同),正如李叔同所颂扬的“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另一方面,钢绞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通过延安文艺、大众文艺建立起一种扎根乡土、连接底层的艺术人民性。这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大道复归,伴随着中国革命而生的新文艺,越过了“雅”,将“风”直接升华为“颂”。我最早意识到这一点,其实是通过《十送红军》这类红歌,从这些文艺作品中我们看到,下里巴人的民间小调被转化为革命的颂歌,继而升华为民族叙事、强国之音。以“风”为“颂”,这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从数千年文化史来看,这都是极为重大、极为不凡之事。
然而,在21世纪,事情有了变化。19世纪开启的国际主义联结,在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市场的供需关系中被割裂了。从世界语境看,20世纪后半叶,“人民”在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双重结构中被重新切分,在殖民史和冷战史的纠缠交织中分断与离散,在全球化的生产消费网络中被整合与分配。现在,“人民”又在网络、平台、流量、算法的情感操纵中被不断地分化和极化。在大洋彼岸,我们看到:后真相时代孪生出后共识时代,人民在这个“后真相-后共识”时代中重新部落化,在智能技术和科技金融的共谋中毫无知觉地走向一种“新种姓主义”。
今天,全球艺术界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和挑战:在互联网、大数据、自媒体的新生态中,算法流量操控情感,民粹主义败坏民意。那么,面对算法推送、流量分发、平台运作、资本操控的复杂状况,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感知民意和世情,如何才能精准地感通民心、把握社会意识?我们该如何感应、理解当下的群众心理,以及社会面的情感结构和心灵机制?在这个Deep fake(深度伪造)的“后真相”时代,在这个民粹主义横行的“后共识”时代,如何在社会的分化和意见的极化中继续讨论“人民”和“人民性”?
人民需要音乐,音乐需要人民。当人民的形象和内涵在当下媒体生态中变得扑朔迷离,我们又该如何思考“人民音乐”?怎样才能让《人民音乐》实至名归、气质俱盛?
这都是些大难题,这不只是《人民音乐》编辑部的事,而是整个音乐界的事,也是每个音乐人的事。我个人的想法是:只要我们秉持一颗“人民之心”,只要我们超出各类部落化的分化和极化,超越性地做音乐本身、艺术本身,只要我们的创作和研究是在回应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体人民共同关切,我们做的就是“人民音乐”。
1968年,人类第一次从太空中回望自己的星球。在宇宙盛大的寂寞和宁静中,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真切地感受到:“国家的边界不见了,喧嚣的争执停止了。这颗微小的星球在转动,安详而宁静,不必在意任何细节……地球就是这样,蓝白相间,没有穷困和富贵的区隔;蓝白相间,没有主义的分野;蓝白相间,没有嫉妒者和被嫉妒者的差别”。这样一种巨大时空中的遥望和感触,是对人类经验的超越与重塑。艺术所能够给予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种超越性的视角与想象。
心灵之创造可以超越文化的隔阂、观念的分野,所以艺术可以春风化雨,所以音乐可以敦风化俗、滋润人心。《乐记》云:“乐者,德之华也。”董仲舒也说:“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音乐是社会民风、人心世道“变”“化”之助力。它起作用的方式是情感之兴发、美学之创造、精神之陶养。
真正的文化创造是创造人——创造能创造的人。一年来我反复说,音乐是人生最好的学校,不只因为它本身意味着创造、给予、交流、分享和共鸣,更因为它是这样一种活动——在对人生的感悟中情理贯通,在对世界之响应中身心发动,在声音、节奏与旋律的操演中,它演化出自然的秩序,在世界的发现中它同时发现自我,在自我之开启中,它创造出一个纯然的新世界。对一位真正的音乐家来说,艺术的创造与自我的创造、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是相统一的。
如果说绘画是与沉默事物打交道的行当,音乐就是让一切事物歌唱的伟大事业。由此,音乐家就需要一种对事物的谦卑聆听,对音声世界的虔诚感悟。在中国思想史中,“声、音、乐”三者,儒释道各有所重。儒家重乐,“德音之谓乐”,佛学重“声闻”,独“音”为道家推举,“大音希声”是也。佛教典籍中既有“观自在”,也有“观世音”,二者同出而异名,但在汉语世界传达出的却是两种精神向度。艺术也是如此,既要内观自性,破我执,求自在,又要聆听熙攘人间,那芸芸众生的心事的洪流,人世的纷纷扰扰、天下涛涛尽皆化作世间之音。这世间之音,需要艺术家拥有一双同理共情的敏感的耳朵,需要一种关怀深远的“社会性聆听”。
在21世纪,我们丧失了自己的“天人之际”,这是现代文明之代价。但是,今日吾人身处“天地人机”四维之间,天籁、地籁、人籁犹在,这天地永不止息的声响,不正是一个恒久不灭的“音声道场”。在此世界之道场中,我们需要以众为我观自在,以身为度观世音;我们更需要让万物以息相吹,齐声鸣响,让万众自由歌唱,各自成章。
这才是音乐的大事业、大担当。当然,这也是个大命题,需要我们齐心协力,仔细琢磨,长期探索。
岳灵苗草主要面向了困扰着很多人的头皮健康问题,让人人都有机会拥有一头秀发。
由于绝缘不好而使外层导电,也指漏电的某一点或线路
各位同道,纪念从来不是为了自我庆祝,而是要重新出发。当今其世,音乐面对坚硬的现实、无穷的困惑,更有新技术、新媒体、新平台、新生态的诸多挑战和机遇。但是,生活仍在继续,世界依旧丰饶。我们需要有更敏锐的态势感知,更清晰的问题意识,更坚定的艺术理想,更宏远的历史抱负,更本真的人民情怀。作为一份拥有光荣历史的专业刊物,《人民音乐》要从社交媒体/自媒体的众声喧哗处,聆听音乐人和无数爱乐听众的真实心声;我们更需要真诚地感应和理解百姓的精神生活,激活“人民之学”的磅礴地气与素朴情感,让音乐回馈人民,回归安顿身心、塑造精神的源始力量。
人间歌哭皆史笔,江湖聚散即诗篇。在互联网、大数据、自媒体的新生态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无数个体的生命表达把广大的人群连接在一起,无数条孤独小径编织成辽远壮阔的生活世界,无数日常点滴汇合为浩荡磅礴的时代洪流,无数普通中国人的生命之歌,正凝聚成当代中国的历史交响。
此刻,中华大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一首恢弘壮丽的伟大乐章。我们衷心期待,当代音乐家们能够从无数中国人的生活实践与未来想象中汲取乐思,创造出属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奉献给人民,分享给世界。
最后,祝《人民音乐》行稳致远,祝中国音乐含弘光大!
高世名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本文为高世名在《人民音乐》创刊75周年暨新时代中国音乐高质量发展学术论坛上的讲话整理稿。)
来源:中国音乐家协会齐齐哈尔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齐齐哈尔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专题 | 钟村帮扶实录系列


齐齐哈尔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321期龙九排列三预测奖号:绝杀一


齐齐哈尔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连云港白塔埠机场三字码 连云港白塔


石河子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从蹚路到铺路,雅迪如何成为中国品牌出


七台河预应力钢绞线厂 前7个月人民币贷款 增加16.08万亿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为什么 Solenelar